本文由网友 夜.未央 推荐
寻访夏洛蒂·勃朗特或者说简·爱的过程浪漫又辛苦。
英格兰的秋天,笼罩着雾和雨,汽车走错了路,在乡间小道上绕来绕去兜圈子,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狭窄的车厢里蜷缩了一宿。
但是,英格兰北方小镇哈沃斯还是在第二天早晨迎面而来,带着湿润的风。
这是个依山而建的小镇,黑色条石铺成的街道保持着中世纪的原形,下雨时不会积水,但穿着高跟鞋走在上面并不舒服。
石头和红砖建成的房子都是百年前的建筑,挂有BandB幌子的是带传统英式早餐的家庭旅馆,价格大致为一个双人间每天50英镑。
山顶的教堂是全镇的中心,很多年过去,石头砌成的老教堂依然结实。
一百多年前,夏洛蒂的父亲老勃朗特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他在这里娶妻生子,领读《圣经》,主持过许多婚礼葬礼,最后,又由别人主持了他的葬礼。
教堂后是偌大的勃朗特家族墓地,年代已很久远,长有不知名的高大乔木。石头坟墓层层叠叠排开,有些歪斜开裂,墓碑上布满苔藓,字迹模糊到无法辨认。有的还装点着鲜花,打扫得一尘不染。所有坟墓的形状不尽相同,越古老就越庞大,无一例外的是都装饰有十字架。
再后面的二层小楼,曾住着勃朗特一家,现在是故居博物馆。
一个多世纪前,夏洛蒂·勃朗特在里面度过了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从画像上看,她是个小个子女人,有着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简·爱相似的容貌,薄薄的嘴唇,面色有些苍白。我注意到玻璃展柜里的素花裙子腰身纤细,针织手套也很小。
英国的城镇好就好在古老,人们普遍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结,举国上下就像一个超级巨大的老古董,几百年来面貌风景变化不大。从英格兰到苏格兰,到处是老街老巷老教堂,粗大的橡树和醋栗树,还有无处不在的人物雕塑,他们的脑袋是海鸥和鸽子最喜欢歇脚的地方,肩膀上常常落满了鸟粪。
哈沃斯也是这样,远离中心城市,几乎没有受到过战争的破坏,又是雨后的早晨,所以尤其显得宁静。
我漫步在潮湿的街道上。一百多年前的夏洛蒂·勃朗特也常在这里漫步,有时候三姐妹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我能够想象出她匆匆的或者舒缓的身影。她穿腰身很窄、下摆撑得很大的素花裙子,头上戴有和简·爱同样的帽子,手中永远有一柄小巧的伞。她微微踮起脚,小心地走过有些湿滑的石头街道,街道在傍晚会有专门的人用长杆点亮昏黄的煤气灯。
那些今早正在飞翔或者暂时栖息的鸟,它们的祖先就曾在夏洛蒂的窗户前鸣叫;那只花园里肥胖的黑猫,它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也应该曾蜷缩在她家的扶手椅上,安心地打着呼噜。
也许某个天气好的傍晚,落霞灿烂,在某条林荫路尽头,真有一位绅士当着她的面,从马上摔下,所以有了后来小说的情节。两人最终过上美满的乡村爱情生活,让读者大大舒口气,心满意足地合上书本。
现实生活中的夏洛蒂·勃朗特没有简·爱的幸运,在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后,1854年6月,她38岁时才和她父亲的同事尼古拉斯结了婚,据说婚后的日子还算美满。但好景不长,仅仅6个月后,她就生了病,不到40岁就离开了人间。
就是在这里,在天气阴郁寒冷、不适合出门的日子,在二楼小小的起居室里,女作家憧憬着心中的爱情,构思并写出了《简·爱》,为全世界能够终成眷属的有情人,还有更多因为世故人情的阻碍而不得不劳燕分飞的男人女人讲述了一个具有浓郁英格兰乡村风味的爱情故事,为她赢来不朽声誉,也使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哈沃斯最终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小说写得跌宕起伏,缠绵悱恻,其间的伤心、绝望、撕心裂肺,到后来的水到渠成、柳暗花明,让人欷歔,慨叹,感同身受。
中国古人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很精辟。其实每个伤痕累累的男人内心深处都是一个罗切斯特,每个罗切斯特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他的简·爱。而每个不幸婚姻的阁楼上,都关着一个会咬人的疯子,她(他)会把美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变成一片焦土,最终两败俱伤。
小说中的罗切斯特是幸运的,而现实中的许多罗切斯特,只能终生囚在幽暗的围城里,郁郁寡欢。
找寻和自己般配的爱人的道路千回百转,曲折又辛酸,虽然不乏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但更多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影,是绝望、郁结、愤懑。
我的一位好友喜欢用“苍茫的疼痛”来表达这种心绪,这是敏感的男人和女人内心常有的感受,不只是为具体的某人某事,也是对人生、时光,对盛宴必散、好景不长的怅惘和预感。你明知道非常重要,想挽留,可就是留不住,只有眼睁睁看着美好的东西渐行渐远,空留断肠人在天涯。
有时候自以为胜券在握,幸福只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婚礼上,牧师已经轻松地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宾朋们想的是宴席的丰盛,只要再等到一句坚定的“我愿意”,就心想事成,却冷不防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或别的什么鬼地方的蓄谋已久的声音冷冷地改变了似乎注定的幸福,蜡烛熄灭,香槟不再冒泡。原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转眼土崩瓦解,甚至来不及反应和辩解。
外表冷漠、生硬、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内心敏感、脆弱、疲惫不堪、孤单凄切,这是罗切斯特,也是天底下大部分的沧桑男人。他们冷嘲热讽,拒人千里,甚至出口伤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痛苦和无助。
只有简·爱这一类型的女人能够打动和安抚中年男人苍茫纷乱的心。她也许会在你春风得意、高朋满座的时候悄悄离去,却注定在落叶无边的秋夜轻轻回归,安静得有如最初的月色。她永远不会是浓墨重彩、光艳逼人的存在,但那种沉静质朴、恬淡隽永,恰恰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宿感。
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样以女作家特有的敏锐洞察了不幸的中年男人内心的压力与痛苦,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主人公简·爱,慰藉着好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不小心弄错终身伴侣的苦涩。
小说自问世以来,打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被拍摄成各种版本的电影,成功地为一批批罗切斯特树立起梦中情人、心中偶像的标准。
电影中脍炙人口的台词是这样的:“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假如上帝给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让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但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我和你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简·爱是流着不可遏制的眼泪说这番话的。
这是简·爱式的独立自主,简·爱式的自由平等,简·爱式的爱情宣言,这是一种被逼迫到墙角的孤注一掷的最后呐喊,是有尊严的弱势群体在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里不屈的绝地反击。
这些话也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心声。
在哈沃斯,我其实根本就分不清夏洛蒂和简·爱的界限,常常把她们混淆为一个人。
我寻访墓地的时候,不熟练的英文开口就是:“请问先生,简·爱的坟墓在哪里?”而那位笑呵呵的英国乡村警察,居然毫不迟疑地就把我领到了夏洛蒂的坟墓前。
我可爱的英国朋友请我品尝老派的约克夏布丁——一种美味的传统食物,她的介绍也是:“简·爱曾在这一带的乡村学校教书。”
我当然知道她的本意是指夏洛蒂·勃朗特,但我乐意听她这样说,并且我一直固执地认定,给我们端上大盘食物的那个健壮的红脸膛英国农妇,她的长相就非常像格瑞斯·普尔——小说中罗切斯特疯老婆的看护,常常偷着喝醉酒。
就要离开哈沃斯了,我还是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简·爱。在我最后一次走过古老街道的时候,久违的太阳已经出来了,暖暖的阳光照亮了小镇,照亮了那对相互搀扶的夫妻,照亮了那给我指点迷津的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他优雅的夫人,而我的心在惜别中,又一次充满了温情。
寻访夏洛蒂·勃朗特或者说简·爱的过程浪漫又辛苦。
英格兰的秋天,笼罩着雾和雨,汽车走错了路,在乡间小道上绕来绕去兜圈子,我们甚至不得不在狭窄的车厢里蜷缩了一宿。
但是,英格兰北方小镇哈沃斯还是在第二天早晨迎面而来,带着湿润的风。
这是个依山而建的小镇,黑色条石铺成的街道保持着中世纪的原形,下雨时不会积水,但穿着高跟鞋走在上面并不舒服。
石头和红砖建成的房子都是百年前的建筑,挂有BandB幌子的是带传统英式早餐的家庭旅馆,价格大致为一个双人间每天50英镑。
山顶的教堂是全镇的中心,很多年过去,石头砌成的老教堂依然结实。
一百多年前,夏洛蒂的父亲老勃朗特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他在这里娶妻生子,领读《圣经》,主持过许多婚礼葬礼,最后,又由别人主持了他的葬礼。
教堂后是偌大的勃朗特家族墓地,年代已很久远,长有不知名的高大乔木。石头坟墓层层叠叠排开,有些歪斜开裂,墓碑上布满苔藓,字迹模糊到无法辨认。有的还装点着鲜花,打扫得一尘不染。所有坟墓的形状不尽相同,越古老就越庞大,无一例外的是都装饰有十字架。
再后面的二层小楼,曾住着勃朗特一家,现在是故居博物馆。
一个多世纪前,夏洛蒂·勃朗特在里面度过了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从画像上看,她是个小个子女人,有着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简·爱相似的容貌,薄薄的嘴唇,面色有些苍白。我注意到玻璃展柜里的素花裙子腰身纤细,针织手套也很小。
英国的城镇好就好在古老,人们普遍有着浓厚的怀旧情结,举国上下就像一个超级巨大的老古董,几百年来面貌风景变化不大。从英格兰到苏格兰,到处是老街老巷老教堂,粗大的橡树和醋栗树,还有无处不在的人物雕塑,他们的脑袋是海鸥和鸽子最喜欢歇脚的地方,肩膀上常常落满了鸟粪。
哈沃斯也是这样,远离中心城市,几乎没有受到过战争的破坏,又是雨后的早晨,所以尤其显得宁静。
我漫步在潮湿的街道上。一百多年前的夏洛蒂·勃朗特也常在这里漫步,有时候三姐妹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我能够想象出她匆匆的或者舒缓的身影。她穿腰身很窄、下摆撑得很大的素花裙子,头上戴有和简·爱同样的帽子,手中永远有一柄小巧的伞。她微微踮起脚,小心地走过有些湿滑的石头街道,街道在傍晚会有专门的人用长杆点亮昏黄的煤气灯。
那些今早正在飞翔或者暂时栖息的鸟,它们的祖先就曾在夏洛蒂的窗户前鸣叫;那只花园里肥胖的黑猫,它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也应该曾蜷缩在她家的扶手椅上,安心地打着呼噜。
也许某个天气好的傍晚,落霞灿烂,在某条林荫路尽头,真有一位绅士当着她的面,从马上摔下,所以有了后来小说的情节。两人最终过上美满的乡村爱情生活,让读者大大舒口气,心满意足地合上书本。
现实生活中的夏洛蒂·勃朗特没有简·爱的幸运,在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后,1854年6月,她38岁时才和她父亲的同事尼古拉斯结了婚,据说婚后的日子还算美满。但好景不长,仅仅6个月后,她就生了病,不到40岁就离开了人间。
就是在这里,在天气阴郁寒冷、不适合出门的日子,在二楼小小的起居室里,女作家憧憬着心中的爱情,构思并写出了《简·爱》,为全世界能够终成眷属的有情人,还有更多因为世故人情的阻碍而不得不劳燕分飞的男人女人讲述了一个具有浓郁英格兰乡村风味的爱情故事,为她赢来不朽声誉,也使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哈沃斯最终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小说写得跌宕起伏,缠绵悱恻,其间的伤心、绝望、撕心裂肺,到后来的水到渠成、柳暗花明,让人欷歔,慨叹,感同身受。
中国古人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很精辟。其实每个伤痕累累的男人内心深处都是一个罗切斯特,每个罗切斯特终其一生都在苦苦寻找他的简·爱。而每个不幸婚姻的阁楼上,都关着一个会咬人的疯子,她(他)会把美丽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变成一片焦土,最终两败俱伤。
小说中的罗切斯特是幸运的,而现实中的许多罗切斯特,只能终生囚在幽暗的围城里,郁郁寡欢。
找寻和自己般配的爱人的道路千回百转,曲折又辛酸,虽然不乏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但更多的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幻影,是绝望、郁结、愤懑。
我的一位好友喜欢用“苍茫的疼痛”来表达这种心绪,这是敏感的男人和女人内心常有的感受,不只是为具体的某人某事,也是对人生、时光,对盛宴必散、好景不长的怅惘和预感。你明知道非常重要,想挽留,可就是留不住,只有眼睁睁看着美好的东西渐行渐远,空留断肠人在天涯。
有时候自以为胜券在握,幸福只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婚礼上,牧师已经轻松地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宾朋们想的是宴席的丰盛,只要再等到一句坚定的“我愿意”,就心想事成,却冷不防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或别的什么鬼地方的蓄谋已久的声音冷冷地改变了似乎注定的幸福,蜡烛熄灭,香槟不再冒泡。原以为坚不可摧的东西转眼土崩瓦解,甚至来不及反应和辩解。
外表冷漠、生硬、玩世不恭、放浪形骸,内心敏感、脆弱、疲惫不堪、孤单凄切,这是罗切斯特,也是天底下大部分的沧桑男人。他们冷嘲热讽,拒人千里,甚至出口伤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痛苦和无助。
只有简·爱这一类型的女人能够打动和安抚中年男人苍茫纷乱的心。她也许会在你春风得意、高朋满座的时候悄悄离去,却注定在落叶无边的秋夜轻轻回归,安静得有如最初的月色。她永远不会是浓墨重彩、光艳逼人的存在,但那种沉静质朴、恬淡隽永,恰恰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宿感。
夏洛蒂·勃朗特就是这样以女作家特有的敏锐洞察了不幸的中年男人内心的压力与痛苦,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主人公简·爱,慰藉着好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不小心弄错终身伴侣的苦涩。
小说自问世以来,打动着一代代读者的心,被拍摄成各种版本的电影,成功地为一批批罗切斯特树立起梦中情人、心中偶像的标准。
电影中脍炙人口的台词是这样的:“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假如上帝给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让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但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像我和你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简·爱是流着不可遏制的眼泪说这番话的。
这是简·爱式的独立自主,简·爱式的自由平等,简·爱式的爱情宣言,这是一种被逼迫到墙角的孤注一掷的最后呐喊,是有尊严的弱势群体在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里不屈的绝地反击。
这些话也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心声。
在哈沃斯,我其实根本就分不清夏洛蒂和简·爱的界限,常常把她们混淆为一个人。
我寻访墓地的时候,不熟练的英文开口就是:“请问先生,简·爱的坟墓在哪里?”而那位笑呵呵的英国乡村警察,居然毫不迟疑地就把我领到了夏洛蒂的坟墓前。
我可爱的英国朋友请我品尝老派的约克夏布丁——一种美味的传统食物,她的介绍也是:“简·爱曾在这一带的乡村学校教书。”
我当然知道她的本意是指夏洛蒂·勃朗特,但我乐意听她这样说,并且我一直固执地认定,给我们端上大盘食物的那个健壮的红脸膛英国农妇,她的长相就非常像格瑞斯·普尔——小说中罗切斯特疯老婆的看护,常常偷着喝醉酒。
就要离开哈沃斯了,我还是不能够确定自己是否找到了简·爱。在我最后一次走过古老街道的时候,久违的太阳已经出来了,暖暖的阳光照亮了小镇,照亮了那对相互搀扶的夫妻,照亮了那给我指点迷津的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他优雅的夫人,而我的心在惜别中,又一次充满了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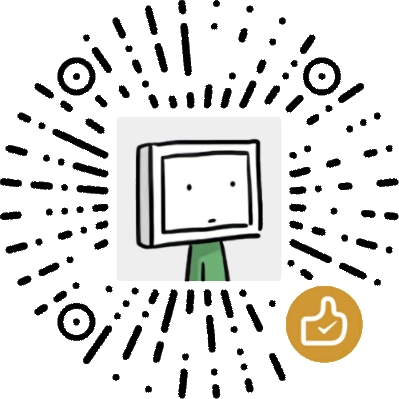

#cmt34
你的GG单价怎样啊 赞助你一个啊
回复